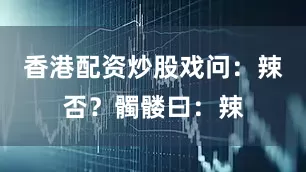
作者:徐琰青
关于北京的文本书写有着极其多元的面向——从明末清初的《帝京景物略》到近代的摄影术再到现代在Citywalk中留下Vlog——北京始终处在记忆与文化叙事的交汇之处。它既是都城,也是市井,既是人们存在的空间地域,也是情感与历史安放、交织的空间。
本期人文清华播客的“清华大课间”栏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冯乃希老师,一起聊聊北京这座城市是如何被一代又一代人“写”出来的。
本期内容
110 北京好写,太好写了!历史文本中的北京城
本期嘉宾
冯乃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明清文学史、近现代思想史、史学文化与理论、性别研究等。著有《都城新生:帝制晚期至现代中国的历史、知识与北京书写》(英文版即将出版),译有《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女性日常生活专题”“知识、观念与文学”等课程。
展开剩余84%蒜泥白肉喂骷髅:“辣辣辣!”
岁五日,中侍例同太医院官来捕虾蟆。嘉靖中,御用监奉御来定,五日方捕,至羊房南大柳下,坐柳根午食。顾旁一髑髅,来濡肉蒜盘,内髑髅口,戏问:辣否?髑髅曰:辣。来惊,去肉,辣音不已。骤驰而归,辣辣音追之,数日来卒。
——《帝京景物略·南海子》
关于北京成体系的文化形象描述在明朝中晚期才出现。其中一部名为《帝京景物略》的作品是冯老师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1629年,文人刘侗从湖北进京赶考。抵京后与友人相携游览北京城,不由得感慨北京之奇,遂以高度诗化的语言书写了许多关于北京的奇闻逸事。
位于北京南部的南海子公园从前是一个皇家猎苑,每逢端午会有大内宦官前去采“蟾酥”。一日,某宦官采罢蟾酥,于柳树下用膳,旁顾见一骷髅,遂将正在品尝的“濡肉蒜盘”(蒜泥白肉)塞进骷髅口中,戏弄之余不忘开口问:“辣吗?”骷髅张口答曰:“辣!”宦官大惊失色,拔腿就跑,骷髅穷追不舍,“辣辣辣”之声不绝于耳。数日之后,这位戏弄骷髅的宦官就一命呜呼了。
北京南海子公园
冯老师表示,这一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学母题,其情节融合了更早的文学传统。在冯梦龙《古今谭概》中“骷髅言”一条也有类似的喂骷髅吃话梅的记载。更向上追溯则有庄子行道见一骷髅,问其死因,骷髅则半夜托梦与庄子谈论生死本质的故事。向后看,1935年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还改写了《庄子》中的骷髅寓言,作《起死》一文。
此外,结合该书的创作背景——晚明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时代——以及作者刘侗与批判宦官的文人团体的关联,我们可以透视故事中蕴含的对当时权势宦官集团的影射与批判。冯乃希老师指出:“他(刘侗)所见所写的北京城——作为首都,北京是政治的中心,其本身就是权力交错的一个场域——所以相关的写作必然不会是简单的、透明的、平铺直叙的,一定会掺杂作者对政治、对权力的见解。”
作为“头脑”的北京
北京何以为都?相比自然环境更加优越的江南水乡,北京堪称“人力堆出来的都城”——粮食靠运河调运,物资仰赖周边供给。但正如顾炎武所说,燕京是中华的头脑。北京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无可替代的“瓶颈”地理格局。冯老师表示:“也许真的是因为北京这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对于东北亚,对于满蒙地区的影响,它的那种对于北方各种民族潜在的团结和向心的力量,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连贯和融汇。”
北京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红尘白日”“水刚土碱”的自然状况催生出了其独特的城市性格:这是一个自古就能够产生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之地。同时,作为都城的北京又被一种很强的管理性所影响,这是一个横平竖直的城市。所以到了明清时期,生活在京都的人是非常懂礼貌的。在这一面向上,北京很重礼法,跟其他地方性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差异。
早在元明清三代,北京就已经是一座高度融合、多元共生的城市。从地理上看,北京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从文化上看,它既是都城,又承载着南北、内外、朝野之间的复杂流动。元明之际,大量蒙古族与中亚色目人定居北京。许多明代将领与后妃都具有蒙古血统,虽然改用了汉姓,但文化上保留了深厚的族群背景。比如郑和就因其穆斯林身份,在文化交流沟通上更具优势,所以他代表明廷出使海外,达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在北京,在特定节令,甚至可以一览护城河里洗大象的风光——这是皇家礼仪的一部分。而骆驼作为常见运输工具,也常随着商贾在正阳门外聚集。北京成为这些多元族群共处的空间载体。
清 丁观鹏 乾隆皇帝洗象图(局部)
“镜”中城:在摄影与文明之间
除了文人笔下的北京,摄影技术的发展也为北京的记录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初,日本东洋史、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带领着摄影师小川一真进入北京进行了所谓的“中国古建筑艺术调查”。这一调查行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直接相关,这些照片常令人百感交集。摄影师跟随侵华军队进入空寂的紫禁城,荒草与汉白玉栏杆相映,在肃穆和荒凉之中又带有一种天然的美感。
小川一真摄,伊东忠太主持:“太和殿”,《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1906年,第一图。
在众多照片中,有一张尤为特别:一面镶嵌在繁复屏风上的镜子,幽幽反射出空无一人的宝座、雕栏,以及深处垂花门的叠影。鉴于当时的摄影能力有限,加之宫殿内部光线昏暗,这样一张照片需要想尽各种办法找光,利用各种各样的光板、光幕来补光,才能获得如此精美的效果。
小川一真摄“乾清宫内镜”,《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1906年,第71图。
除了外国摄影师展现的视角,中国人也进行了自己的摄影实践。中国对于北京的系统性拍照,是在1935年年底完成的《旧都文物略》。这与300年前的《帝京景物略》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
20世纪30年代,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就在此时,北平政府决定要开发文明——将这座明清遗留的旧都,描绘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城”“古都”“文明的结晶”。他们组织修缮、拍摄城墙,绘制导览地图,最终完成了《旧都文物略》这部作品。这项工程在知识界内部引发了强烈争议:支持者赞成以文化自救、保存民族记忆,利用文化城对侵华者进行一定威慑;而反对者则认为,在百姓流离失所、资源极度匮乏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城墙、搞摄影、印图册,无异于“舍本逐末”。
冯乃希老师指出,不同的人对于救亡构想的差异在此刻展现,每个人的议程都在历史巨变的特定时刻体现出来,这也是做北京研究一个非常迷人之处。
“胶囊”北京:City walk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如果将来有人回望我们这一代人眼中的北京,回看这一代人对北京的记录,会从什么角度读出我们的情感与立场?冯乃希老师说,随着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发生变化,我们这一代的记录者或许有一种City walk的心态。
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对于城市的记录将会是散步、骑行,探索城市犄角旮旯里那些堆叠的感觉。走在北京胡同街巷中,有些建筑可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造成厂子或留下了公社的痕迹,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成为商店、商场。在漫步时,我们会发现特别细小的时空折叠的面相。
比如海淀区知春路边的“卫星厂”,曾是“东方红”卫星的制造基地,后来成为字节跳动的办公楼。而如今,“卫星厂”已经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文化聚点,咖啡馆、酒吧、live house、艺术展、集市纷纷落地其中。
北京卫星制造厂
“北京很有特色,像一个胶囊,浓缩式地看见不同时代的痕迹,这很有意思。”冯老师说,“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北京这种对称性的互补结构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版权声明】本文原载于“人文清华讲坛”,出于信息分享目的转载。相关权利归原作者及原平台所有,若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
发布于:天津市杠杆配资业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